悦读.浪荡子与革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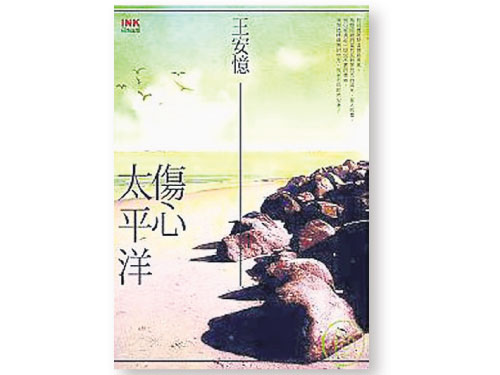
作者:王安忆
出版社:印刻
特约:张斯翔
回到新山休假的某日午后,刚下过的雨水刷走了各种热,房里闷闷的没能察觉,原来走到院中,已是清凉如水分子悬浮冲刷空气般。和台北不同的平房,和邻人共用一道薄薄的墙,能传来各种远近车响,野狗家犬相互对嚣,还有邻家孩童游戏的笑闹。这是生活的杂讯,是常在台北老旧四楼公寓盘居的我,早已远离甚久的气息。
我靠着墙憩坐板凳之上,半顶着灰蓝的天,读那逆寻根的《伤心太平洋》,自身从岛屿星罗棋布的太平洋一端到另一端,驿马星动的人生。我从不眷恋土地,也许正是那一种海洋的命运使然。母亲总说自己还好能独立,否则总有各种事一个人独居恐怕无法完成。
我是家中漂流最远之人
“我觉得,我爷爷家,是养育革命者和浪荡子的摇篮,这便是爷爷奶奶伤心的源泉。革命者和浪荡子全是漂流的岛屿性格。”王安忆如是说。
我可能是家族里这一辈人,漂流得最远的那个,我不可能是革命者,恐怕只能是浪荡子。祖父在过番后走卖货物维生,从未安定于某处。甚至死亡,都没能给我们留下一个确切的时间或空间。家中的神主牌是他唯一的依归,他流落不知何方的肉身早已灰飞烟灭,唯有在这块不大的木片之上,他的魂兮归来,才与自家血脉用文字回归到了一处。
我们这一姓的男子,都在漂流中各自寻活,也许正应了祖父留下的血脉或无坟的祖坟风水。静坐片刻也终得起身,转身,然后离去。
“你必须离开你出生的地方,你也不能太早开始全职工作,你需要离开的力量和方式,这就是你的命。”相士如是说。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太虚幻境早就写好我运命的簿册,抑或我受了相士的暗示,竟真的从新山出走到吉隆坡,然后再漂流到台北。
我不禁想像,散居南洋的华人流行的唐山探亲,到了我这一代,也许就会反过来,成为散居各地的人,为了寻根而远赴南洋,如王安忆一般循着先人的足迹,寻找埋藏血缘的那一坯土。南洋曾在几代人的眼中,是离散前往之地,然后我们这些浪荡子,却让南洋承载了根,或就用理论式的说法:“根化”了。
跨越半个太平洋的乡愁
王安忆的乡愁跨越了半个太平洋,太平洋成了她庞大的漂流系统与离散投射,她早就已经是十足的“中国人”了,可是因这曾在海上漂流的血脉,却让她总在海洋路上逆寻她的祖辈悲剧的源头。像逆流而上的鲑鱼,总想回到自我生命的发源处,可或许,真正回到自己血脉出生之地,却发现原来什么都没有;又或许和自己曾经想像的早已不同,从一种离散,走进另一种离散。
最后,文学或是曾经记下的文字,方才能锁住那些曾经的过往与生命流注的轨迹。诗成为生命的血液,流送于大陆与南洋诸岛屿之间,记载了那些坚强与软弱。
所以,两篇中篇组合成了一本书,不断诘问:诗是什么?是命运;命运是什么?是诗。然后回望过往,生命面对时代的断裂,产生了海洋式的命运,而后成就了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