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客室.週末架勢堂 年輕的心有間電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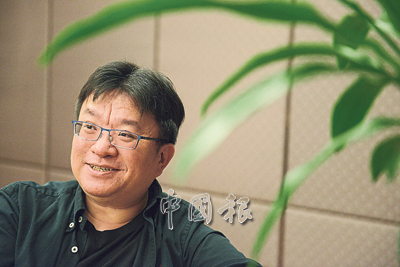
特約:子若
圖:楊智聰、受訪者提供
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聞天祥
此番,趁著這位曾出任金馬獎、台北電影節、香港電影節、亞洲電影大獎等電影盛會評審的他,踏著“2015金馬創投會議”宣傳的列車而來,《架勢堂》自然不放過機會與他談談他的戲夢人生。
最近與電影人或是熱愛電影的人,特別有緣。早前有結合電影、佛教和人生說故事的國際藏傳佛教喇嘛導演宗薩欽哲仁波切有過一席之談,今天,則來了一位把看戲當作人生理想,以信仰般態度視之的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聞天祥。
如果宗薩欽哲仁波切被人封為“亞洲最會說故事的導演”,那麼,聞天祥則有“台灣最年輕的資深影評人”稱號。他之所以得到這個稱號,就因為16歲開始,就在報章雜誌發表電影文字,20歲起歷任各大報章雜誌影評人及專欄作家。
對看戲看出許多學問的他,還以“蔡明亮研究”取得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后來,策劃五屆台北電影節(2002-2006),為它樹立了年輕、獨立的新形象。
2009年則被侯孝賢導演延攬,出任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至今(現任主席為張艾嘉導演),2010年成功帶領工作人員創辦了活力十足的金馬奇幻影展。
中學時期電影院開拓視野
跟大部分的孩子一樣,童年時的聞天祥,就開始對看戲這件事產生莫大興趣,出生于1969年的他坦言:“那個年代也沒有太多的網絡游戲呀!”
恰恰在他成長中的70年代,是台灣文藝電影和香港武俠片的全盛期,他以一句“看得亂七八糟”來形容那一段看戲的舊時光,“我什麼電影都愛看,部部電影之于我都是不可思議,並且找到喜歡它的理由,看完后都非常開心。”所以,長輩帶他去看電影,是頗有成就感的。
單純的興奮感,支撐他一直都在看電影,身邊的師長也沒人會認為,他這樣熱愛看戲,是可以看出一個有希望的未來,因為“電影評論員”從來就不被視為一個可以維生的正業,“但是,家人也沒反對我這麼沉迷于看戲。”
周記寫看戲心得
一直到了中學,必須到台北這個大城市唸書時,台北的電影院是他開拓視野的地方,打下紮實且豐富的看電影基礎,“那時候,隨身攜帶一本小小的英文筆記簿,每看完一部電影,就把它的導演、攝影和演員的名單記錄下來,然后再添加一些觀后感受。”
當時的讀書生涯裡,老師規定班上同學每個星期都要呈上一篇周記,撰述在一周內發生的國家大事或個人生活記事,“我卻有點叛逆,嘗試把看電影的事寫給老師看,以試探老師的反應。”
令他開心的是,老師不但不指責他,反而公開讚許他的行為,“老師覺得,這樣的周記內容,不只是讓他有機會瞭解我,同時也有助于他對電影的認識。”語畢,他開心到呵呵大笑,並且說道:“這位老師,可說是訓練我當影評人的第一人。”
一個好老師,就是對每一種類型的學生都有深刻瞭解,並以包容心待之,這樣一個小舉動,往往成就孩子的整個人生,聞天祥可說遇見了好老師!
影評影像結合
才能具體印證意義
自從獲得老師誇讚后,聞天祥每週都寫一篇關于電影的周記,“中、英文片子都寫!”有了一段日子的磨筆之后,他開始想,是不是可以寫得更好、更工整一些,以作投搞用途。
他自認為可以攤在陽光下被讀者檢視的第一篇影評文字,是寫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他把這篇稿子投給了台灣最具分量的電影雜誌《世界電影》(這雜誌成立于1966年,擁有最豐富完整的電影、明星資訊,以及重量級影評)。
“該影評文字被刊登了,無疑是對我的莫大鼓勵,所以就繼續寫了。”基本上,當時的他對影評文章並沒有特別概念,只是每觀看完一部電影就有感想,“看多了,自然就會開始細究某部電影的優缺點,于是我開始翻閱各種海內外的電影專業書籍。”
電影除了培養他的閱讀習慣和嗜好,他也勤于參與各項電影活動。那時,台北有座藏書豐富的電影圖書館,礙于年齡限制,導致他不能借書,而參與了館外電影劇場的觀賞電影活動。
“媽媽遞給我1000塊台幣,去報名參加這個活動最便宜的課程。”結果,在兩個月時間裡,他過足看戲的癮,大量觀賞了英格褒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年)、伍迪艾倫(Woody Allen,1935年)等導演的藝術電影。
尚記得,他先是閱讀了主辦機構發給參與者的電影文章,然后,乘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到會場,與一群志同道合者擠在一個空間不大的地方,對著一個小電視機,他笑言:“眼睛要睜得很大,才看得清楚該部電影哦!”
隨身攜帶電影書籍
每看完一部電影,踏上回家的路上,他就馬上找出相關導演的文章來閱讀。他聲稱,隨身都會攜帶電影書籍,以應付不時之需。在這過程中,他最大的體會是,唯有把電影文章和影像結合起來,才能更具體發現和印證一部電影的實質意義。
回家后,他就開始把自己腦海中的想法化為文字,並把三五千字的心得報告寄給報章、雜誌,或學校的校刊。
“文章是越寫越多,文字是越寫越長,這些演變都在顯示自己對電影的發現更多、感想更豐富,並且很樂意跟讀者分享。”聞天祥的影評人生涯,從此掀開序幕。
每個人天生都是影評人
在談撰寫影評文章的過程中,我聽到重複率頗高的一個字眼是“發現”。到底,愛電影愛得如癡如醉的聞天祥,他在電影裡發現了什麼?他的發現,與普羅大眾有什麼不同嗎?
“我倒不覺得一定有不同之處,只不過,我不太甘心只看到電影表面上所呈獻的故事樣貌。”對他而言,這不過是創作者引導觀眾進入他的世界的一個引子,“我們作為觀眾,要如何吸收糖衣下的營養,這才是最有趣的部分。”
每觀賞一部電影時,他都會主動找出這部電影怎麼會這樣拍、故事為何如此說,以及為什麼要這樣運鏡。他總是絞盡腦汁解構導演的創作手法,以及自己的觀后想法。
他認為,這是一種探索與學習的過程,“我要知道為何別人的發現,跟我的發現不一樣?誰又被誰說服了?憑什麼堅持己見?”
儘管此前未曾在電影科系正式上過一堂課,但,所有他觀看過的電影都是他的課本,許多的影評人是他的導師,在這過程中,種種發現是他選擇繼續“閱讀”和“書寫”電影世界無可取代的動力。
不反對影評主觀判斷
從看戲到評戲,他的文字成了與電影愛好者的橋樑,“我每次都會想像我的讀者群,他們應該是一群與我同樣愛看電影,卻不是讀電影系的個體,恰恰他們都是喜歡文字的人,所以通過文字來體會我想告訴他們的事。”
他認為,每個人體內都會有評戲的細胞,“因為每次看完戲后,不管好看不好看,都會向身邊的人發表感想。”而他撰寫的影評,只不過把主觀感受運用(看似)客觀文字來傳達觀后感,他認為,我們所有擁有的理性知識,其實是幫助我們進入電影世界的工具,最終需要自己做出判斷。
至于他的這些文字為何具有參考價值,他是這麼認為,“實際上,讀者是透過影評人看電影的方式,延伸到其背后看世界的方式,這是吸引和留住讀者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並不太反對影評裡摻著主觀判斷,“這些主觀都是相關影評人的獨特發現,它具有參考價值,甚至可以刺激讀者進一步思考人與電影之間的關連。”
由于聞天祥畢業于輔大中文系,他不諱言,在撰寫影評時需要有一定的考量,不能說是包袱,但終究有文字能力去駕馭影評文章。
所以,文字的佈局對他而言很重要,從報章的影評欄目、副刊到學術刊物,都得採用不同的書寫方式,以應對不同層面的讀者群。總的來說,若要當上好的影評人,影評文字要寫給誰閱讀就很重要。
正因為這樣的學術背景,他年紀輕輕就寫得一篇篇四平八穩的影評文章,“加上一個具有古早味的名字‘聞天祥’,素未謀面的雜誌主編都不疑有他,繼續採用我那些年還是青年時寫的文章。”
有了這些個電影專欄的磨練,他在大學畢業后,就把影評人當作正職。在巔峰時期,他幾乎每天早上都在寫作,中午開始看電影、泡圖書館,晚上到大學電影社帶學生。他的文章常見于《中時晚報》、《自由時報》、《聯合報》、《民生報》、《工商時報》等各大報章,以及《世界電影》、《幼獅少年》等雜誌。








